
第二場
主持人:范文謙 山西博物院副院長

報告一:山西古代造像碑的數量、分布與移動
王煒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王煒從造像碑的基本概念入手,認為山西保存的古代造像碑時代連續、數量眾多且內涵豐富,一方面雕鑿有精美的宗教造像,另一方面還承載著造像記、布施人等大量的文字信息,包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這些造像碑最晚從明代已經見于著錄,主要見于各地的地方志、金石志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造像碑作為一種重要的石刻資料受到學術界的持續關注。據他統計,山西現存古代造像碑約500通,其中收藏在各級博物館、文物機構等約300-400通,保存在室外的約100通,僅存著錄的約100通。他從對山西古代造像碑數量的整理和統計入手,一方面對造像碑現在的時間分布和空間分布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與分析,另一方面,考慮到造像碑的位置大多經過位移,側重分析造像碑在近代以來的移動情況,并深入分析了造像碑與石窟寺的“代償”關系。

評議人:劉巖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
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他將這么多可移動、不可移動的造像碑進行了非常基礎性的、普查性的梳理,而且制定了詳細的研究路徑,意義重大。第一,他開啟了一個系統性研究的新的方向,從本質上說還是一種考古學研究的方法,基于分期和分區研究的考古學傳統研究的范式,但是這種基礎的資料之前沒有人做過系統的梳理和研究,里面有很多紀年的材料,這樣把一個一個時空上的“坐標點”還原到原始出土的地點上,對于從區域分布、造像碑沿革歷史來探討山西民間信仰、宗教信仰這方面來說有很大的意義,期待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報告中還提出了在不同政治、經濟等條件之下,在共同的信仰之下,不同人群對信仰供奉的不同表現方式,提出了造像碑與石窟之間的“代償”關系,也是一種新的認識。

報告二:《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立碑時間考
郝軍軍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郝軍軍首先指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是研究云岡石窟的重要文獻,原石碑早已不存,碑文幸存于清人傳抄的《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條引《析津志》文中。碑文為皇統七年(1147年)曹衍撰寫,但這并不是立碑時間。他從碑文中避諱情況以及出現的武散官名稱,判斷立碑時間在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金世宗改名完顏雍至金章宗明昌初年之前。他指出,熊夢祥抄錄碑文時,完全忠實于原貌,再一次證明了碑文內容的可靠性。
評議人:劉巖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
“金碑”是宿白先生早年發現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對于云岡石窟斷代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碑已經不存,碑文經過輾轉抄錄,郝軍軍老師從細節入手,從遼代“咸雍”“壽昌”兩個年號在金代文本中出現的形式切入,認為是金世宗避諱的結果,而且還更進一步地考證了一個是避金世宗自己的諱,一個是避金世宗嫡母壽昌的諱。文章還從“經武將軍”這一名稱出現時間上來推定立碑時間的下限。這篇文章的意義有兩方面,第一是從細節方面出發細致地考證,進一步論證了“金碑”這篇文獻的可靠性;第二,這個研究其實也引出一個現象,也引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在皇統年間撰文,在大定十四年之后立碑,這之間有十幾年的時間差,中間正好差了一個海陵王,那么這就是個有趣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他的文章中也還有別的類似的情況,那么就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請人來寫碑文到這塊碑立起來,中間是有時間差的,甚至是十幾二十年,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視角。具體到云岡石窟來說,是不是金熙宗、海陵王以及后來的金世宗他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影響到了云岡石窟的修繕和增修等活動,這可能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那么再擴大一點的話,這種碑文寫碑和立碑的時間差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如果是,也是值得研究的,我們期待進一步的研究。

報告三:晉東南地區北魏晚期至東魏通肩禪定佛研究
武夏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武夏從“如何確定造像的尊格”入手,從題記、特殊姿勢、固定組合、經變圖像、造像題材的意義等方面展開闡釋,介紹了晉東南地區北魏晚期至東魏石窟呈現一定規律性的造像組合,其中主尊佛像著通肩袈、裟施禪定印,其他兩壁主尊造像則著外衣搭肘式袈裟,施無畏、與愿印,指出通肩禪定佛是為了與其他佛像作出區別而采用的不同佛衣與手印。武夏對比同時期其他地區石窟及造像碑中同類型的佛像,初步推定晉東南地區這類造像尊格為無量壽佛,同時通過與周邊地區造像風格比較,認為這一佛像樣式應是受到關中地區的影響,探討了中原北方東部地區北魏晚期至東魏時的西方凈土信仰。

專家評議
評議人:杭侃 云岡研究院院長
武夏老師從一種特殊形制、特殊位置的造像組合入手,她認為是無量壽佛,這個觀點我覺得很有啟發。看了她的對比材料,我又想到南涅水有一塊造像碑,這塊造像碑的功德主說他的祖先是從甘肅東部過來的,那么這就可以和武老師的研究連成一條線,也就是說無量壽的題材從炳靈寺——隴東——長安,然后是晉東南,都有,如果它們之間有聯系,還可以和移民考慮在一起。我還想到兩個問題,一個是王煒老師在做的造像碑。
我們過去在著錄造像碑的時候,比較注意發愿文,但對有的造像碑里的人名關注不夠,但是這個名字,包括村名,對我們現在研究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就很重要,王煒老師和楊菊都注意到了造像碑上的所有信息。但是,如果有的造像碑上沒有這么多信息怎么辦呢?武夏老師又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讓圖像去說話,我們同樣能夠去研究這些問題。這個可能是考古學的一個所長,也就是說我們還可能有別的研究方法,所以我覺得武夏老師的研究一個是它的具體研究,第二個可能從方法論上,從圖像研究的角度進一步深化我們的研究。
說到造像碑的話,包括后來段老師說到的交通問題,我就想到另外一個問題。思考造像碑和石窟與寺院關系的問題的時候,如果是石窟,尤其是大一點的石窟,更多的是因崖建寺;但是對造像碑來說,可能是造像碑因寺立碑。比如說《洛陽伽藍記》里記載的平等寺造像碑。由于造像碑可以搬動,所以要研究造像碑所在的寺院信息,就要像王煒老師說的,要找到這些造像碑的原始位置。我想地方志應該再梳理一下,因為地方志里面可能有寺院的信息。所以說因崖建寺和因寺立碑,研究的空間還比較大。

報告四:對中國古代石窟選址與交通道路關系的
反思——以晉冀地區北朝中小石窟為例
段彬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段彬認為古代石窟的選址往往與交通道路具有一定關聯性,前人對此多有論述。然而既有研究對這種關聯性的認識存在簡單化的傾向。事實上,石窟選址受到人地關系的多重因素影響——適宜開窟的山體巖面、契合教義的地理環境、主體信眾的居住地與交通線的走向,共同決定了石窟造像的位置。因此石窟與交通道路之間存在不同情況的復雜關系,石窟的選址既可能靠近道路,也可能刻意遠離通衢。道路附近石窟造像的數量、規模,與交通線的重要程度未必成正比。在小比例尺地圖上看似靠近道路的石窟,實際也未必與道路相鄰。考察石窟造像選址時,更應該立足于具體微觀的地域、階層和造像契機,以開鑿者的視角進行思考,選擇大比例尺地圖或衛星圖進行參考,最好親臨其地觀察地理環境,而非基于宏觀地域的“他者”視角一概而論。考察石窟選址的交通因素時,應注意區分直接位于某條交通線上亦或處于交通線輻射范圍內兩種情況。反之,通過石窟判定古代交通路線,還應當結合文獻記載和地理狀況的判斷,不應將佛教遺存作為道路狀況的唯一依據。
評議人:杭侃 云岡研究院院長
段老師的發言表現了年輕人大膽假設,在研究方面敢于質疑的勇氣。我想具體問題的探討,還是要宏觀和微觀相結合。宏觀上來說,石窟寺和交通線的關系,應該是可以成立的。為什么我說宏觀上來說可以成立呢?比如說,我對河南的中小型石窟做過調查,東魏、北齊的石窟主要分布在太行山東麓,洛陽附近的北魏石窟主要就是所謂的龍門的衛星窟。東魏、北齊的石窟集中分布在太行山東麓,就是因為遷都鄴城。張慶捷老師他們探討晉陽和鄴城之間分布的石窟,就是晉陽和鄴城聯系多了之后,沿線東魏、北齊的石窟就多了。所以我想,石窟寺的分布與交通線路存在著一定的關聯,大體上來說是沒有問題的。具體的問題還要具體分析,比如不同時期詳細的交通線路,段老師考慮得更為細致,這個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的。除了他剛才舉的那些例子之外,我想稍微補充一點,就是這里可能還有宗派的問題。比如說,劉慧達先生寫過《北魏石窟與禪》,“鑿仙窟以居禪”,自古名山僧占多,深山藏古寺,都是說有些石窟距離交通線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在《洛陽伽藍記》《魏書·釋老志》等文獻里面也都記載過,許多寺院位于繁華之地,所以考慮這個問題,還可以看看嚴耕望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等著述,就是說我們考慮起問題來應更全面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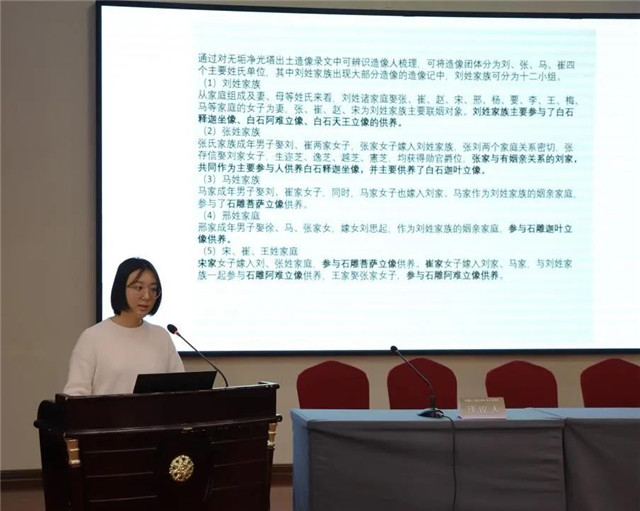
楊菊 山西博物院 山西大學云岡學博士研究生
楊菊從佛光寺無垢凈光塔的調查與造像發現過程入手,以圖片的形式系統展示了山西博物院所藏6件佛光寺無垢凈光塔白石造像,指出這些造像早于佛光寺東大殿建成時間百年,具有共時性,最初組合應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通過分析造像記,她認為造像團體來自河北博陵邑陘邑縣劉姓、張姓兩大家族,以兩家族為主導,具有姻親關系的家庭共同參與,彼此以地域為基礎,以血緣和婚姻為紐帶,進行造像供養宗教活動。在此過程中,寺院及造像團體中的僧俗弟子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批造像既延續了北朝以來河北地區造像的部分傳統因素,同時又受到了唐王朝不同時期當時政治中心(長安、洛陽地區)新造像風格的影響。造像材質優良、加工精細,具有濃郁的寫實風格,是唐代造像中的精品,對于研究唐代佛教造像藝術、佛光寺與河北地區僧眾聯動、《大無垢凈光陀羅尼經》傳播及民眾信仰都具有重要價值。
評議人:劉巖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
一提到佛光寺,我們一般對它的古建筑比較感興趣,聚焦于這一點。天寶十一載(752年)的這批造像材料的披露,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方向。對于佛光寺,我們不應該僅僅聚焦在古建筑上。2014年,我們考古所也對佛光寺做了考古工作,重點在于對佛光寺的布局進行探討。楊博士的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從比現存佛光寺東大殿更早的宗教文物材料入手,作了一個研究和探討。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來構建或者說還原佛光寺的沿革,從豐富它的文化內涵方面作出有益的探索。具體里面一些詳細的內容,比如說河北幾家人家的新造像或者造像的佛教風格、來源、具體宗教活動就不再細說,但是我覺得她也是開啟了一個方向,就是我們從多方面來重新復原、重新還原、重新構建歷史中真實的佛光寺。

李雅君 山西大學美術學院
李雅君對山西藝術博物館所藏的“大周大云寺涅槃變相碑”進行了深入分析,從圖像內容出發,分別解讀了“入般涅槃圖”“純陀最后供養”“金棺自舉”“自啟棺蓋”“為母說法”“雙足顯圣”“佛棺自燃”“八王分舍利”“起塔供養”“須彌山崩”等圖像,探討了在特定的時間、地域內新的圖像內容的產生與相關經典的關系,并分析了圖像源流和流傳過程中其表現手法、風格樣式的沿襲,揭示了其所蘊含的豐富信仰內涵與思想。
評議人:杭侃 云岡研究院院長
李雅君老師的題目我很感興趣。為什么感興趣呢?就是我覺得山西的東西太好了,涅槃碑是64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純陽宮里面有兩個造像是禁止出境的。我想在其他省早就研究得很透徹了,但是這兩塊碑我們能檢索到的研究成果不多,這兩尊造像的研究我們應該加強。當然,圖像的解說是一方面,我更想聽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圖像,但是李老師講完圖像的內容就結束了。其實圖像構成其他學者也在探討,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呈現的現象。比如說《山西古跡志》里面也記載了其他的涅槃碑,文獻里記載涅槃碑當時建有重閣,重閣上尊像的組合等問題也需要關注,所以我們期待李老師以后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