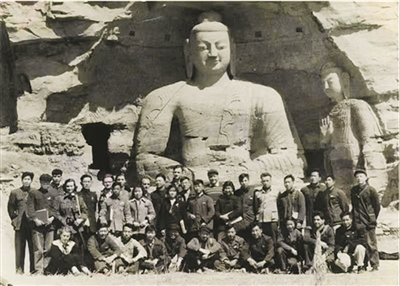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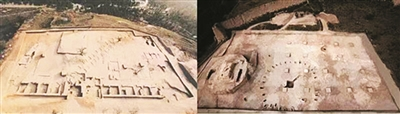
前輩學者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眾多成就,杭侃認為我們應該考慮從新角度來研究云岡石窟。云岡石窟開鑿在砂巖上,保存下來的題記很少。但云岡石窟的三期洞窟中均存在著大量的補鑿龕像、打破關系和未完成的窟龕,這些遺跡現象對于深入研究題記留存很少的云岡石窟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因此,他希望學界對云岡石窟的打破與補鑿遺跡、未完成的龕像進行調查和記錄(包括文字描述、攝影、部分實測等),并整理、編輯調查報告。他嘗試對云岡石窟各洞窟的年代、洞窟原來的布局設計,和洞窟中后期的開鑿工程進行考察,從而從一個以前沒有加以系統注意的角度,推動云岡石窟的進一步研究。
比如關于云岡第20窟西壁坍塌的時間與曇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設計的討論,杭侃認為,從遺跡現象的打破關系來看,曇曜五窟當初是計劃把第19窟作為主窟,按照昭穆制在左右各開兩個洞窟。不過,工程進行途中第20窟發生了崩塌,因此將本來應該修建在第20窟西側的第16窟的位置移到了東側,也就是說16窟原來計劃開鑿在21窟位置。中央第19窟是太祖道武帝,按昭穆順序,左側第18窟為第二代明元帝,其次右側第20窟為第三代太武帝,下面本來作為左端的第17窟是太武帝之子景穆帝,最后本來作為右端的第16窟是景穆帝之子文成帝。
此外石窟內還有一些未完工的現象,部分洞窟的裝飾以及造像的輪廓、服飾部分已經完成,但面部尚未雕刻,可能是最后才進行面部開光這一步驟。所以一個大型石窟工程的開窟時間和完工時間可能會間隔很久,甚至涉及到停工。為了研究石窟中一些現象形成的原因,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還于鞏義進行了佛教實驗考古,對鞏義石窟的一個北魏龕像進行了開鑿復原。通過本次實驗,可以引發一些問題的思考,比如開鑿工程量以及石料去向等問題。細化至具體問題,我們還可以思考第5、6窟是否是一組雙窟。第二期石窟中,一般認為7、8窟最早,9、10窟次之,5、6窟已經快到遷洛時期。5窟主尊是云岡石窟里面最大的,肯定是皇家所開,第5窟和曇曜五窟的形制接近,同樣是馬蹄形窟,主尊占據了窟內的大部分面積,題材上以三世佛為主,背光火焰紋依舊屬于第一期的樣式。第5、6窟開鑿的時間可能有間隔,第5窟的右壁和第6窟的左壁最薄的地方只有2厘米,現在有個地方都已經通透了,這種情況只有第5、6窟有,可能是開鑿有先后,出現設計上的不周造成的。推測第5窟開鑿的時間應該緊接曇曜五窟,裝飾紋樣等輔助性裝飾是獻文帝時期完成的,后因某種原因中斷了工程,孝文帝親政后完成了大像部分,所以這個石窟表現的不是一個時期的風格。另外巖體規劃、云岡的洞窟排年、北魏時期云岡的面貌等很多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杭侃簡單介紹了對曇曜五窟開鑿工程的重新思考,包括選址、斬山、設計、施工以及曇曜在具體設計的時候可能遇到的問題。首先在選址時利用河流階地以減少工程量,并且選在最寬處,以使窟前面積最大化。另外,這條河流旁還有一條通往和林格爾的路,在交通方面也很便利。《魏書·釋老志》中記載“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可見當時工匠對大型石質工程的石質還不夠了解,斬山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可能有多次改造,這種現象在云岡中也常常見到,比如中區一線大窟與相鄰的13窟以及16窟附近等,這些在考慮洞窟排年的時候都需要思考。曇曜在設計時,選用的題材為三世佛,以宣傳佛法。使用的窟形為大像窟,模擬皇帝。
此處有一邏輯問題,即來自涼州的僧人曇曜為什么沒有采用涼州和敦煌早期流行的中心塔柱窟呢?杭侃認為文化的傳播不一定是線性的,中間還可能會有“插播”的現象,有待專文探討。至于窟型是仿草廬還是氈帳,杭侃更傾向于是氈帳,是一種創新,突出帝王的地位。另外,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石窟開鑿的很多,但是窟前并沒有多少位置,那么平城時期的僧人居住的寺院在哪里?考古工作發現云岡石窟東西兩側以及頂部都有北魏時期的寺院分布,也有遼金時期的,所以說那個時期的僧人是住在山頂的,呈現《水經注》所記“山堂水殿,煙寺相望”之景。
三、云岡學建設的思考
談到云岡學的建設,杭侃認為應該從云岡在歷史中的地位出發,建設的內容可以借鑒敦煌學的內容,但云岡學和敦煌學的研究各有其側重點。具體而言:
1.敦煌學研究的內容是區域性的,云岡學的研究內容是全域性的。敦煌位于邊關,而云岡是位于都城的。
2.敦煌學研究的內容側重微觀,云岡學的研究內容在做微觀研究的同時,需要對北中國地區的早期石窟和宗教遺存做宏觀的研究。
3.云岡學和敦煌學都研究石窟,云岡石窟尤其是其遷都洛陽前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洞窟,是皇家意志的藝術化表現,出資開鑿者為皇室和上層統治者;敦煌石窟多中小型洞窟,其出資開鑿多為地方官員和僧侶。
4.敦煌學研究的特色內容是其出土的文書,云岡學的研究內容除了正史,還有平城地區重要的考古發現,以及在云岡模式影響下在北中國地區出現佛教遺跡和碑刻題記。
新材料會帶出新問題。云岡學的建設,在城市與聚落、民族融合、墓葬、手工業、宗教遺存、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會不斷提供新的材料。而云岡學的建設需要依靠山西省內尤其是大同本地的考古和文物資源,對平城時代的遺跡和遺物都要有充分的關注。
杭侃將云岡學建設的核心內容總結為三個層級,分別是云岡石窟的研究和保護、北魏平城時代考古資料的研究和保護、云岡模式的廣泛影響。
講座尾聲,杭侃表達了對云岡學建設的愿景。首先是基礎資料的呈現。基礎資料的呈現面臨許多困難。手工測繪效率低,但是我們也無法依賴先進的測繪手段,因為測繪的問題實質上是對對象加以認識的問題,人認識不到的問題,測繪機器不會幫助人去辨識。因此,最根本的問題在于,現在全國從事石窟寺考古的專業人才很少,需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總之,中國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編寫,任重而道遠。另一個愿景是多學科交叉研究,包括考古學(中古時期考古、佛教考古)、歷史學(民族融合、古代社會治理、歷史地理)、哲學(宗教學、美學)、物理(巖體力學)、化學(文物保護)、地質、中文(民俗與方言)、美術(雕塑、從人文角度的美術史研究)、音樂(音樂史)、生物與醫學(古DNA、同位素等)、旅游(文化遺產活化、文化創意產業)、計算機(大數據)等。進行云岡學研究要有大的知識體系,多參考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不能故步自封。
最后,杭侃表達了對云岡學未來建設的信心,并以宿白先生的話與大家共勉——“致學存乎心,補拙莫如勤”。















